多乐棋类游戏:
1983年4月的北京,春风已吹绿了长安街旁的国槐树梢,玉兰花刚打了浅白的花苞,花瓣上还沾着晨露。可三里地外的秦城监狱,铁栅栏上的霜气还没散尽,墙根的枯草在风里抖得发颤,庄严得让人喘不过气。
北京市中级公民法院的法槌重重落下,“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十八年”的宣判声,像石子砸进静水,透过法庭的高窗传得很远。站在被告席上的男人,头发已有些斑白,发缝里还嵌着几丝洗不净的灰,从前昂着的下巴垂了下来,眼里的精光全被麻痹替代,只要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袖口磨破的毛边。
谁能想到,这个从山东威海渔村泥滩里爬出来的穷小子,曾一度站在权利的中心圈层。中心工作厅代主任的头衔,让他在特别时代里,成了红墙内炙手可热的“红人”——文件要经他手批转,会议要听他定调子,连当地大员见他,都得赔着当心说话,那股威势,足以让整个京城的干部都胆寒。
更让人无法宽恕的是,他把公民赋予的权利,变成了虐待忠良的屠刀。彭德怀元帅那具皮开肉绽的遗体,肋骨断了三根,手臂被拧得脱臼,临终前连一口热粥都没喝上;还有那些被他罗织罪名的干部群众,有的家破人亡,有的含冤入狱,这些冤魂的血泪,都成了他人生最漆黑、最洗不掉的注脚。
前史的镜头拉回五十年前,1931年的威海卫,黄海上的风波卷着咸腥的水雾,一遍遍拍打着码头的青石板,也拍打着少年戚本禹赤脚走过的生长之路。那时候的他,还叫“小禹子”,跟着父亲在码头上捡他人漏下的小鱼虾。
1931年的山东威海,渔民们靠海吃海,可北洋水师毁灭后,这儿成了外国商船的停靠点,本地渔民的渔网常被轮船螺旋桨绞破,日子总被风波掀得乱七八糟。戚本禹的出世,没给这个靠父亲搬卸洋货维生的贫困家庭带来高兴,反而多了一张要吃饭的嘴,母亲常抱着他坐在门槛上哭。
海风里的咸腥味,和家里米缸见底的困顿,是他幼年最深入的回忆。牵强在村里私塾读了四年书,十三岁那年冬季,父亲在码头被英国商船的木箱砸伤腿,他就辍了学,接过父亲的麻绳去搬卸棉花和洋布。粗硬的麻绳磨破他幼嫩的手掌,血泡破了又结茧,可他从不喊疼。
可戚本禹脑子活,不甘心一辈子困在码头当苦力。他人罢工后聚在酒馆喝残次烧酒、打牌赌钱,他却躲在自家漏风的小屋里,点着豆大的煤油灯,啃着从旧货商场淘来的旧书。四书五经、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,更难以想象的是残缺的《资治通鉴》,什么都看,遇到不认识的字就记在手心,第二天问私塾先生。
命运的起色出现在1949年。新我国建立的礼炮声,不只响彻广场,也顺着渤海湾的海风传到了威海的小渔村里。18岁的戚本禹,凭着一手整齐的毛笔字和识文断字的本事,自动参加村里的土改作业队,帮着写斗地主的材料、挂号田产,活跃体现得让队长都称誉,如愿参加了我国。
在其时的乡村青年里,党员身份是极大的荣誉,意味着有时机脱离渔村。戚本禹比谁都清楚这是改变命运的第一步,干活分外拼命。土改时带头冲进地主家清算浮财,扫盲夜校里,他把杂乱的字编成渔民了解的“渔网歌”,让目不识丁的渔民几天就学会写自己的姓名,这些体现都被记在了干部档案里。
1950年的冬季,威海下了场稀有的大雪,码头结了冰无法干活。就在戚本禹以为要断粮时,公社干部踩着雪送来一封牛皮纸信封的调令——中心工作厅秘书室的选用告诉。烫金的“中心工作厅”五个字,在雪地里分外耀眼,像一束光,完全照亮了他的前路。
初到北京的戚本禹,像刘姥姥进大观园。红墙内的琉璃瓦、秘书室里那些北大、清华结业的搭档,说着他听不明白的“术语”,都让他感到骨子里的自卑。他第一次穿中山装时,乃至把纽扣扣错了都没发觉,被搭档偷笑。但他很快冷静下来,理解光靠卖力气不行,得有“过人之处”才干站稳脚跟。
他开端像在码头调查货品相同,调查身边的人和事,揣摩领导的心思。他人静心收拾文件只做外表功夫,他却会把文件按领导重视的要点分类,用红笔标出要害句;开评论会时,他从不简单讲话,等领导和老搭档说完,再捡着最贴合领导思路的观念弥补,每句话都说到点子上。
这种“会来事”的特质,让他逐步被秘书室主任注意到。更重要的是,他的笔杆子逐渐显露出矛头。每次写报告材料,他都能把单调的数字和作业,用生动的比方串起来,比方写扫盲效果,会详细到“某村张大爷学会写家信,激动得哭了”,条理清晰又有温度,总能捉住领导的目光。
1956年,戚本禹被调到《红旗》杂志社,这成了他人生的“黄金跳板”。这份由中心主办的理论刊物,是其时思维宣扬的中心阵地,社长是大名鼎鼎的陈伯达,在这儿作业,意味着能非直接接触到中心的理论动态,离权利中心更近了一大步。
起先,他仅仅个一般修改,担任校正稿件、给资深作者收拾材料,每天泡在堆满旧刊物的材料室里。可他不甘心做“暗地影子”,总想着“搞点大事”高人一等。他翻遍材料室的太平天国史料,发现史学界对李秀成的点评存在争议,马上意识到这是个“博眼球”的突破口。
其时史学界的干流观念,以范文澜、罗尔纲等我们为代表,都把李秀成视为“太平天国后期的国家栋梁”,以为他的《自述》是“困厄中的无法”。戚本禹却反其道而行之,花了三个月时刻写就《评李秀成自述》,直言李秀成是“苟且偷生的叛徒”,是“太平天国的罪人”,言辞尖锐,观念极点。
这篇文章在《红旗》1963年第13期宣布后,马上引发轩然。北大前史系专门开了评论会争辩,《前史研究》等刊物纷繁转载。争议声中,毛主席在一次中心会议上说到这篇文章,翻着刊物说:“这个戚本禹,有点思维,敢说话,不像有些学者畏缩不前。”这句点评,让戚本禹的命运完全起飞。
声望有了,官运也跟着来了。1966年,特别十年的前奏摆开,思维宣扬作业被推到前台,戚本禹因“敢言敢写”被任命为《红旗》杂志副主编。这一年,他才35岁,穿戴笔挺的干部服,收支中心机关,和曩昔在码头搬货的穷小子,早已是大相径庭,正是神采飞扬的年岁。
更惊人的选拔还在后边。1967年,中心工作厅人事调整,戚本禹靠着“紧跟形势”的政治姿势和之前堆集的声望,一跃成为中心工作厅代主任,直接担任中心机关的文件流通、会议组织等日常作业。从威海渔村的泥滩到红墙内的工作室,他用了不到二十年,完结了旁人几辈子都未必能完结的逆袭。
可权利这杯酒,历来都简单让人醉。站在权利的高峰,戚本禹很快忘了自己是谁——忘了码头搬货时冻裂的双手,忘了入党时“为公民服务”的誓词,忘了威海渔村里那些和他相同的穷苦人。他开端享用他人的阿谀奉承,把权利当成满足私欲、镇压异己的东西。
1967年的北京,街头的标语贴满了墙面,“砸烂旧国际”“横扫全部牛鬼蛇神”的赤色大字扎眼耀眼,戴着红袖章,举着语录本在街上高喊标语,疯狂的声浪此伏彼起。戚本禹坐在中心工作厅三楼的工作室里,窗外便是长安街,他看着下面涌动的人潮,心中涌起的不是对乱局的忧虑,而是掌控全部的振奋。
他清楚地知道,这是个“乱中取势”的时代。手中的权利越大,能做的“大事”就越多。而在他歪曲的认知里,所谓的“大事”,不是安稳局势、维护干部,而是经过冲击异己来稳固自己的位置,靠踩着他人的骸骨往上爬。越是有声望、有声威的人,打倒他们越能显示自己的“威望”。
第一个被他盯上的,便是彭德怀。这位在朝鲜战场上打出“谁敢横刀立马,唯我彭大将军”的开国元帅,因在庐山会议上坚持真理、批判“”中的过错,遭到不公正批判,此刻正在四川三线工厂“劳作改造”,参加德阳重型机器厂的建造,和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作。
戚本禹为何非要跟彭德怀过不去?外表是“呼应运动”的政治投机,实则藏着没解开的私家恩怨。1965年一次中心作业会议上,评论前史人物点评问题,戚本禹借着评李秀成的风头高谈阔论,彭德怀当场打断他,指着他的讲话稿批判:“文风浮躁,不明白前史就别乱讲话,李秀成的境况你底子没搞懂!”让他在几十位高级干部面前下不来台。



多乐游戏全部:他曾是中心工作厅代主任大举虐待彭德怀1983年被判刑18年!


 029-88894724
029-88894724 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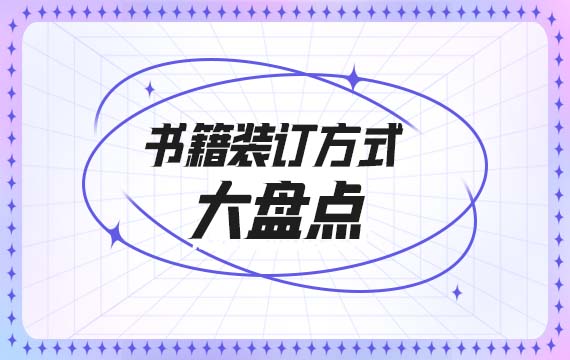
 在线咨询
在线咨询 

